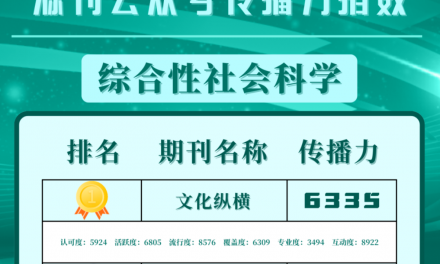4月12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和《文化纵横》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特朗普2.0时代的国际变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召开。会议聚焦当前国际局势变化,围绕“全球范围内新右翼与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特朗普2.0时代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冲击”、“14 亿人的工业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等三大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全国各地近30名专家学者参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他指出,特朗普再次执政对世界格局造成极大冲击,社会思潮的变化是深层原因。在国际失序加速演进的关键节点上,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待与会专家基于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比较研究,共同为促进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深化区域国别学发展贡献智识。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右翼保守主义呈现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隐性反自由等新特征,正在分化西方价值同盟并推动全球南方整合。当前中美博弈已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向国家利益直接冲突。这一变局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通过引领全球南方国家重塑国际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变局中构建新的发展范式。
本次会议的第一项议题由《文化纵横》执行主编陶庆梅主持,4位学者围绕“全球范围内新右翼与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逐一发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郭小雨首先指出“保守主义”的激进化造成其概念界定困难,从而突出了“保守主义”力图保守之内外秩序的持续模糊性。她通过讨论柏克与斯密在“价值”产生方式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歧,还原了保守主义用维持价值差来支持政治秩序的特殊方式。最后,郭小雨基于保守主义视角,讨论了美国当前保守主义的深层困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昊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标志着美国保守民粹主义进入新周期,其本质是传统保守主义与极右翼民粹的合流。特朗普通过强化帝王式总统权力、改造共和党为“忠诚党”、推行“单一行政权理论”,试图将白人至上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化。这种做法的实质是通过重构“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美国霸权。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助理研究员赵丁琪以美国左派内部反思为线索,对“进步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即美国民主党所持有的将新自由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相结合而形成的理念。他认为,正是因为民主党过于注重身份政治,忽视了美国底层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文昕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了俄罗斯保守主义如何被建构和使用,合法性源自何处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不稳定性和主观性。俄保守主义的认识来源的重点在于构建或选择性重塑“真理”和“传统”,亦诉诸宗教和特定历史目的论。这种知识生产方式与来源在后帝国语境下仍有诸多矛盾,深刻塑造了当代俄罗斯政治表达与实践。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在对上述发言进行评议时强调,及时而准确地把握美国变化着的现状及趋势依然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学界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不为美西方的剧变所困惑,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专注于自身发展,构建相应话语体系和身份定位,通过与美西方的长期共存、合作与竞争,展示文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的多样性,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让全球选择更美好的未来。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黄靖在发言中指出,特朗普2.0时期全面回归杰克逊主义,试图通过美俄关系正常化重构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平衡。特朗普以关税战重塑贸易体系以孤立中国,然而美国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债务危机和社会分裂等结构性问题持续恶化,加之中国等国家的坚决抵制,将迫使特朗普最终回归谈判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认为,过去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经结束,世界正变得多极化、有界化。曾经各国互相合作、资本自由流动的无边界状态正在消失。如今,各国开始重视自身利益,全球规则面临重构。资本和政治的合作破裂,全球治理机制失效,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正在瓦解,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更复杂、多元、竞争激烈的新阶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基于特朗普2.0时代的特点,认为未来世界局势的演进将与俄乌冲突的解决方式有很大关联。在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下,世界格局将从一超多强走向群雄并起的“新战国时代”,其中中美关系将体现为竞争性共存的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主任徐坡岭教授从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理解、全球化终结的逻辑和关于中俄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民主的三个角度,阐述了中俄合作在为未来全球秩序提供价值观基础、推动双边与区域合作、以及应对大国竞争等方面的进展与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曹远征教授主要从当前美国对世界秩序体系的摧毁、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这一秩序体系的贡献和当今世界对中国经济状态的认知三个方面着手,讨论了全球治理体系在当前激烈变局中的处境与可能的未来。
华中师范大学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严鹏从历史视角剖析全球工业地理变迁,指出特朗普时期产业政策的传统根植于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思想,而中国工业化的观念渊源可追溯至古代“实业文明”。历史与现实的互动警示,在工业地理重塑背景下,中国须兼顾制度创新与观念引领。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琪轩教授以非洲为例,解析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动因。西方“结构性调整”在非洲失效,而中国通过国企主导基建建设,带动了中外企业投资,促进了工人技能提升及产业集群形成。作为“最不可能案例”,非洲借助国际资本、全覆盖的中国制造和改变的生产结构,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封凯栋从内外两个维度来看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和创新问题。他强调,当下14亿人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市场容量、逆全球化等巨大挑战,中国工业输出是解决长期结构性矛盾的必由之路。与美国工业创新的军事底层逻辑不同的是,中国需重构一种适应自身结构性转型的新型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李寅介绍了美国管理资本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多元化运动到金融化、全球化的衰落历程;并且指出美国产业政策陷入“激励与能力脱节”困境。这启示中国需要推动能力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指出,中国发展除全球化外还依赖强大的国家组织和动员机制。中国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实现崛起,是主动适应并突破结构性限制的结果。而美国则因资本逻辑失衡、忽视社会利益而逐渐衰退。尽管中国推动全球合作带来新希望,但也要警惕他国反感与未来被全球化反噬的可能,尤其要关注产业空心化和内部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当今世界,中国更应“强内功”,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学界应紧扣时代需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